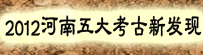>>更多专题
独辟蹊径 勇往直前——记考古专家李绍连先生
时间:2013-09-12 来源:河南文物工作 作者:晨 光 字体:大 中 小
如果说1966年“文革”以前的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是“元老”文物工作部队的话,那么李绍连就是最后报到的一名新兵。1965年7月,他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本科毕业后,直接分配到该队。虽然同年有3名同学分到队中,因为他是最后一名报到者,在老同志眼中,他是个年轻的新兵。迄今,经历40多个春秋,他虽年近古稀,已从新兵变为一个考古专家。
一、新兵多向扬帆
他在校时专攻新石器考古,四年级时在严文明先生指导下撰写学年论文,题目是《论豫北龙山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关系》,其观点主要是两地龙山文既有共同因素又有明显差异。五年级做毕业论文时则在苏秉琦先生指导下,经历半年时间的外出考察,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标本资料室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最后写成了《关于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分期问题》的论文,将仰韶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及地区类型的一些相关问题。因此,他对中原新石器时代考古比较熟悉,并准备专攻之。
(一)初出校门当打杂工
但是,文物队是事业工作机构,当时还不是研究所,不能用人所长,学生的理想难变现实。他是憨厚老实的书生,任凭领导安排进行工作,指西不往东。但零碎的工作安排,性质迥异的业务,使他不得不从事不同工作,四处奔波,好象在无边的大洋中多向扬帆,似乎没有目标,没有彼岸。
1965—1967年在队图书室整理图书。他整日抱大摞各种图书,翻阅内容后,将图书分类编号。该项工作极其简单枯燥,多数人不愿为之。他却觉得也有好处,认为这是熟悉队内图书资料的好机会,有利于日后搞科研。
1968—1971年跑零差,他孤身只影,常常到各市县去干“抢救”文物差事。其中在郏县“三苏坟”院紧急清理了苏东坡侄子苏适(音括)墓,出土二合墓志,铭文表明苏轼苏辙葬此地。在文革中,由于“破四旧”极左思潮的影响,地面文物遭受严重破坏,地下文物亦被殃及。他认为能当抢救队员亦光荣。
(二)始务正业,搞田野考古
1969年,文革进入所谓“整改”阶段,文物队被合并入河南省博物倌,但工作性质未变。1972年后被派往浙川县抢救即将被丹江水库淹没的下王岗遗址。毕业七年之后,首次正式参加考古发掘,他很高兴,犹如漂泊海洋日久,忽然看到朦胧的海岸一样。当时仍是动乱的文革时期,物资非常缺乏,生活十分艰苦,他们还得和民工一样,一天8小时窝在探方里,铲土、挖灰坑、剔人骨,另外还要记录、绘图、照相等忙碌不停。况且该项考古工作就像这个孤岛(当时发掘工地周边已是江水)一样,是同当时社会氛围不协调的,埋头工作却不被群众理解。好在是孤岛,周边对工程干扰并不大,也是幸事。值得安慰的是单位领导和淅川县文化局对这项发掘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发掘进展顺利。淅川下王岗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西周文化等丰富文化内涵,是我国文革中的重大收获之一。他在老同志的支持下,首次正式进行较大面积的发掘,清理了一个有450座墓的仰韶文化氏族公共墓地,取得较大成绩。
为尽快将这批考古资料公布于世,不久就让发掘者开始资料整理,准备撰写考古报告。对于文物队而言,是队领导首次放手让年青人去掂笔杆,挑重担。“谁发掘谁整理”对今天来说已是常规,而当年则是破天荒的事啊!
(三)刚瞄准学术目标就尝到甜头
1977年冬,文物队领导决定组织一个专门寻找新石器早期遗存的小组,李绍连是成员之一。首先到密县莪沟北岗遗址发掘,旗开得胜。在两次发掘的2700余平方米面积中,发现了房基6座、灰坑40余个、墓葬68座。事前未料到裴李岗文化遗存如此丰富,特别是此前在新郑裴李岗遗址未发现房基,莪沟遗址的半地穴圆形和地面方形房基便成为典型范例,是确认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有传承关系的主要因素之一。
1979年,李绍连和一些同志到长葛县石固遗址搞试掘,继续寻找裴李岗类型早期文化。经过几个月的发掘,证明此处是比莪沟遗址内涵更丰富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不料正得意时,领导调他回队在室内整理淅川下王岗遗址发掘报告。后来,郭天锁等同志继续发掘石固遗址,收获很大。
1980年,曹桂岑同志组织淅川遗址发掘组的同志,分别由曹桂岑、杨肇清、李绍连、刘式今等整理发掘资料和分工撰写有关报告部分初稿。最后交给李绍连按报告体例通撰成《淅川下王岗》考古报告书稿。次年定稿并由他送交北京文物出版社。后经送苏秉琦先生审阅,又经曹桂岑、杨肇清与李绍连一道再次修改定稿出版。
(四)又一次偏离轨道,苦苦求索
事业刚有苗头,又有变故。《淅川下王岗》考古报告完成后,正值文物队改建为“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又从河南省博物馆中分立出来。李绍连仍归属文物研究所,不过无安排具体业务,却多次被上级抽调去充当“抗旱”或“农村工作”等工作组成员,搞社会工作了。他毫无怨言,把工作做好。
1981年初,河南省文物局成立,急需人才,傅月华处长将李绍连调到麾下工作。当时李绍连无职务却赋于主管地下文物和田野发掘工作的权力。由于工作对路故能积极地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不过时值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雁南飞”成为时尚,羡慕广东家乡的腾飞,他曾有返乡念头。于是他成功地联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并被接受,只是当时河南正搞机构改革拒绝放人。此事造成人事关系尴尬,他只好走人——调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只身负责筹建考古研究所。
(五)热爱河南文物,矢志搞考古
李绍连在北大学考古,得知河南文物极其丰富,所学的课程中,无论是原始社会时期考古文化或商以后历代考古文化,大都以河南文物为标本,所以在校时就认为“搞考古到河南将大有作为”。因此,毕业分配时他填志愿到河南来。他的导师苏秉琦先生亦鼓励他到河南,后来当苏先生得知他想回南方时还批评过他呢。从此他表示要在河南搞一辈子考古。他积极筹建考古所,无非是表明他矢志不移而已。
河南省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后,因未取得田野考古发掘权,不能从事发掘。但他不放弃,以另一种方式考古——即从事河南考古资料的学术研究。听他说过:“人离文博界,心在考古中”。由于工作需要,他又被调到该院历史研究所,但除了历史课题如《河南通史》他不得不承担外,他仍以考古文化研究为主。他撰写100余篇学术论文和出版的几部学术专著中,均以河南考古文化为主要内容,足见李绍连先生仍是河南考古圈中人。
二、自辟蹊径,勇往直前
人不在文博界,即使他是考古学出身,因为考古文物资料所有权和文博工作平台在身外,难以利用,缺少文物考古工作者种种优越条件,不可能运用第一手资料进行前沿考古研究。经过深思熟虑,他毅然决然地独辟蹊径,走立足河南,面向全国,运用丰富的考古资料,结合历史文献,研究悬而未决的历史和文化问题,即“非田野考古”之路。方向一经确定,锲而不舍,必有收获。事实上,他在学术上有了很大收获。其实这条路也是田野考古之必然延伸。
(一)专门研究新石器时代文化
根据自己的知识专长,李绍连确定在考古领域的主攻方向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发掘密县莪沟遗址后,立即与中原新石器文化做对比研究,撰写了《关于磁山·裴李岗文化的几个问题——从莪沟北岗遗址谈起》论文,综论各地发现的早期文化,并在1980年笫5期《文物》上发表。它表达的裴李岗文化不是中原最早的文化以及与仰韶文化之间有一定的缺环之观点,仍有预见价值。
同时,他深入研究中原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认为这个文化不仅内涵丰厚,而且是中原承上启下的关键文化,认识它就等于掌握了一把原始文化库的钥匙。因此,他下功夫收集资料,研究相关问题,撰写了《仰韶时期社会进化论》(见1986年3期《史学月刊》)、《仰韶文化社会形态初探》(见1986年《中原文物》特刊)等系列论文。
为更好地认识中原原始文化,借发掘淅川下王岗遗址的机会,研究南北两条大河文化关系。他撰写了《试论中原和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论文,首次涉及南北文化关系,指出长江南北新石器文化平行发展,但中原文化影响了江南文化。
(二)为了解原始文化而研究民俗搞史前考古,需要多种学科知识,即地质学、古生物学、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社会历史学、民俗学,从及各种文化专门史等专门知识。若不具备这些知识,则无法判定所发现的史前文物和遗迹的年代,无法解释原始人的事迹,也就无法独立开展史前史和考古文化研究。其他学科知识,一般都可以在课堂学到,唯有各地民俗因地而异,切不可以偏概全,更不能以彼地之俗释此地之民事,因此,它不可能在教科书中一一学到。为了能够诠释史前事迹,特别是各地迥异的葬俗,李绍连独自广泛收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民俗资料,进行分折研究。他说,此举对史前文化研究很有裨益,并不断地在论文中以民俗资料做佐证,获得好评。
繁衍后代,是人类的本能,也是人的社会责任。而很好的合法的婚姻关系,是保证人能生育健康后代的关健。遵好友林家有(中山大学博导教授)的建议,把所收集到婚姻习俗汇集成书,并以《古今中外婚姻漫话》为书名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1987年),出乎意外地热销,广受民众欢迎。本书不仅有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婚俗,更展示了中国56个民族的古今婚俗,反映了婚姻史的发展侧面。能对社会产生良好的作用,正是他所企盼的。不过省内某些学者误会他要搞婚姻研究而嘲笑,实则为他搞史前文化所收集的部分民俗资料而已——即副产品。为严肃学术,他表示不再写任何通俗读物了。
(三)开展中国文明专题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掀起一股“文明热”。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然而对中国文明最早起源于何时何地的问题?却仍是悬案!李绍连认为他是搞的史前考古,文明起源正是其研究的领域,便把此专题作为研究前沿,全力以赴,深入研究。
李绍连为此而做了一个计划,全面收集资料,撰写一系列论文发表。其中有 他的论文《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线索及其启示》(见《中州学刊》1987年第1期),此文曾在1986年全国考古学会沈阳年会上宣讲,因其主张“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的观点新奇,被各媒体抓住并纷纷以“有学者认为中国文明起源有四大区域”为题报道炒作,大报小报几乎都报道,与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论并列,一时引轰动。媒体报道虽不能准确反映“多元论”的观点,但是此后“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却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应该说媒体功劳也是大的。
因这篇论文引起意外的反响,他更努力地搞文明专题研究。他又搞了一系论文发表,主要有《“文明”源于“野蛮”——论中国文明的起源》 (见《中州学刊》1988年笫2期),《试论华夏三部族在中国文明史中的作用》(见《中州学刊》1990年第3期),《既述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见《中国文物报》1988年12月2目第3版),《试从淅川下王岗文化遗存考察文明起源的历史过程》(见《中原文物》1995年笫2期),《伊洛河系文化是中国早期文明的主源》(见《洛阳考古四十年》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从不同侧面反映他的“多元论”学术观点。从这些论文可以看出,他搞文明专题研究是全面和深入的,并不是赶潮流或应时之作。后来他在系列研究论文的基础上,先后又撰写和出版了自己的两部相关的学术专著,即《华夏文明之源》和《河洛文明探源》,则说明他功底之深和努力的程度。一个专题两部学术专著,对一个学者而言也是少见的。
(四)从考古到治先秦史
1991年,因工作需要李绍连从考古研究所调到历史研究所,任主管科研的副所长。职责的变化使他不得不从考古转为搞先秦史。因为先秦史史料匮乏,现代治史者欲有作为不可不借助考古资料。而这正是他之所长。他首先搞原始社会中后段的仰韶文化时期的社会史,由此溯上延下,以了解中原始社会史。其中他主攻关键的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的传说与史实问题,取得成功。他撰写了《炎帝和黄帝探论》(见《中州学刊》1989年第5期),论证了“炎帝”“黄帝”是后人加冠的称号,但他们不是传说人物,他们实则分别是生活在黄河中游地区的姜姓和姬姓部族的首领,是历史真实人物,分别是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创造者。后来李又写了《炎黄二帝与中华民族文化》(见《光明日报》1989年10月25日三版),《涿鹿之战与华夏集团》(见《中州学刊》1996年第1期),《传说时代黄河流域的远古先民》(见《黄河文化史》第一章第二节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等,研究考古与历史的结合问题,建立中原原始社会历史的框架。
除了史前史问题成堆外,夏、商、周三代历史也还有不少问题。尤其是外国史学界迄今仍不承认夏代史,只承认殷墟甲骨文发现后的商代历史。虽然“老外”不承认的夏商社会史也是真实存在的,但中国史学家对此亦必须努力深入研究,解决诸多疑问。李绍连对此自担一份责任,开始一系列课题研究。
首先,他将夏文化和史料结合研究夏史。他撰写了《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大国》(见《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论文,运用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从国家政制、官制、赋税、法律、监狱、军队到经济、文化状况,以论证夏代国家的真实存在。
其次,对商代有丰富的文字和考古资料,是他着力研究的重点,结果他写了系列论文。其中主要有《商代农业生产者的身份初辨》(见《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殷的“上帝”与周的“天”》(见《史学月刊》1990年第4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双为“毫”》(见《中州学刊》1994年笫2期),《试从前后二都剖析商代社会》(见《郑州商都3600年学术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中原诸侯国与商廷的关系》(见《2004年安阳殷墟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科文献社2004年),《关于商王国政体问题——王国疆域的考古佐证》(见《中原文物》1999年第2期)等,从不同视角阐述商代历史。
周代史文献资料较多,考古资料亦丰富,正好解决一些存疑问题。李绍连风趣地说,周史不是己之长,只是主编河南先秦史时未能找到合适的人才,被迫无奈才硬着头皮——赶鸭子上树啊!为搞周史大费周折,除广罗资料,分析疑问,还要突出地方特色,一句话:难呀!知难而上,他研究一些存疑问题。如西周为何要进行大规模分封呢?为此他撰写了一些论文,其中《周初实行分封制度因果论》(见《第三届西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朝华出版社2004年),即以史实分析当政者不得不实行分封的几个社会历史原因,及其最终导致诸侯与王室分庭抗礼和诸侯国间混战的恶果。这是一针见血的论文。
李绍连所有这些研究和努力都是有成效的。最终的成果是由他主编和撰稿的《河南通史》第一卷册(先秦史)出版。
三、几部学术专著的评析
迄今,李绍连被分配到河南工作已40余年了。由于河南优越的考古工作环境,以及他个人的努力,在考古业务工作和学术研究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显著成绩。因此,他在1992年被评为考古学研究员,1993年被评为对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据粗略统计,在省级以上的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著作(包括合著)10余部。限于本文篇幅,在此仅将他个人的几部学术论著略做评析,以飨读者。
(一)《华夏文明之源》是李绍连的第一部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学术专著,1992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它包括了他几乎所有相关论文的观点。书中认为以所谓文明三要素作为文明起源标帜是片面的,主张必须结合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及家庭、私有制和阶级等因素考察国家政权的出现。该书深入研究相关资料后,认为中国文明起源是多元的,其发祥地至少分布在黄河、长江、珠江和北方四大区域的九个地区,最早的国家政权是在中原地区出现,其时间为仰韶文化晚期,距今约4700——6000年之间,很可能在距今5000年前后。本书主张文明起源“多元论”,并非忽略中原是中华文明最早的核心的发祥地的地位和作用。
(二)《河洛文明探源》是李绍连的第二部专门探讨文明起源的专著,虽然与《华夏文明之源》的目标是一样,而资料、内涵以及方法、视角却大为不同。如果说前者是着重阐述“多元论”,那么,后者则是着重论证河洛地区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和核心的发祥地。两者相辅相成,可以说是姊妹篇。《河洛文明探源》一书还通过立国于河洛的夏商周三代国家形成中华传统文化,阐明河洛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中的主流地位和重大影响。
(三)《永不失落的文明——中原古代文化研究》一书,1999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这是李绍连个人从事古代文化研究的综合成果。本书内容丰富涉及到中原古代物质文化、先进的科学技术、兵器与兵法、诸家哲学思想、儒学圭臬、古代宗教、古代爱国主义等方面,但书的宗旨是强调中原古代文化的特征和特色,以及其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史中的主导地位。还要强调的是它属于中华地域文化中的核心地域文化,它的兴盛具有关键作用。其主旨是企图阐明中华文化长盛不衰的原因。而书中第十二章前八节只是八方蕴藏着奥秘,其中地大物博、儒学一统、自主发展三条才是古代长盛不衰的关键。此书获2001年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四)《河南通史》是河南省社科重点科研项目,由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主持,河南大学、郑州大学参与的大制作。其中第一卷册先秦史是由李绍连主编和撰稿。《河南通史》作为地方史主要用地方历史和考古资料写成,地方色彩鲜明。2005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广受好评并被评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社科院特等奖。
李绍连主编的第一卷先秦史,有几个特色:其一,将史料与考古相给合,理清中原原始社会史的脉络,搭建史前史框架;其二,首次将中原文明起源写入正史,将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70年夏禹立国前,视之为早期众小国家的襁褓期;其三、将夏视为统一中原的第一个王朝;其四、用大量甲骨文和考古资料描述商代社会形态;其五、突破“王朝史”体例,设置“社会生活”章节,写一般平民百姓生活。由于体例创新,观点新颖,获得老一辈史学家的好评。
此外,李绍连还出版过个人和与他人合著的著作几部。其中,如1989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淅川下王岗》考古报告,还荣获1991年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他曾为该书出了不少力去撰稿、通稿,但因是集体成果而不想多说什么。至于一些不是理论专著,或层次不够高的著作,亦不想多谈。由此可见李绍连先生对自己要求较高,亦比较谦虚。
学术至高无上,终生矢志学术,是他坚定不移的信条!年近古稀志更坚!我可以相信他还将有更新更好的学术著作问世。